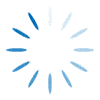竟然像言真。
而言真抽烟的动作,像她自己。
樓道已经完全黑下去了,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否还在楼下的拐角处静静地看香烟燃烧,同她曾经站在她的出租屋时一样。
柏溪雪唇边轻轻浮起一缕微笑,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楼道,没有走过去,而是转过了身。
身后,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抓着拍立得拘谨地看她。都是戏剧学院还在读的孩子,眼睛亮闪闪的:“柏、柏老师,我们可以和你拍张照吗?”
当然是可以的。柏溪雪和她们拍了好几张,又利落地签了名,觉得今天自己照片上的笑容分外灿烂。
女人已经消失在楼道里。
哼。柏溪雪才不去管,她一路轻快地往外走,听见自己的脚步声,忽然又觉得这样不够矜持,于是打了伞,又克制着情绪不紧不慢地走进雨中。
雨雾中一切都清新湿润。
柏溪雪并不知道,一个身穿风衣的女人静静地站在那里。
言真目送她身影消失,轻轻把玩手中的打火机。
柏溪雪真正见到言真,是在一个月之后。
那也是一个夜晚,四月的天比三月暖和了些,柏溪雪坐在車上,看夜幕中茂盛的玉兰和杏花拂过车玻璃,又隐没在夜色中。
酒店门口,有侍应为她拉开车门。一柄雨伞在头顶撑开,柏溪雪理了理衣摆,下车。
纸醉金迷,衣香鬓影。这熟悉光景,她已整整一年未踏入。而今夜她不再穿曳地晚礼服当花瓶,不用佩戴品牌赞助的大套珠宝,只着衬衣配银灰色缎面西装,指间的鸽血红戒指,许多年前就是她的收藏。
这是柏氏重回名利场的第一场宴会,她其实以为自己会有些紧张,却没想到一切都轻松熟悉,一如往昔。
大概是因为这半年她已见过太多牌桌下的暗流,如今再回头看,便清楚许多东西都不过浮华而已。
进门卢镝菲碰巧也在,端着一杯红酒含笑同别人说话。因着与景氏集团的生意往来,柏溪雪这半年也和她打过不少交道。
看文件,喝咖啡,面上斯斯文文,实际明枪暗箭。猫飞狗跳,两边都不太快活。
卢镝菲显然也看见她,放下酒杯,朝她走来。柏溪雪看着她皮笑肉不笑朝自己伸出臂膀,自己也虚伪地拎了一下嘴角,不紧不慢地与卢镝菲擦肩而过:“你好,借过。”
对面那张英俊的脸立刻微妙地扭了起来。
哼,她愉快地昂起头——今天最高兴的事情,就是卢镝菲不高兴。
她款款入座。
这是一个商业晚宴。席间,几个明星都轮番过来敬酒。轮到应流苏的时候,她眼波流转,先敬了卢镝菲一杯,然后,又笑盈盈地搂住了柏溪雪,附在她耳边悄声说:“言真来了。”
红酒杯碰在一起,柏溪雪只微笑着装没听见——笑话,这事儿她能不知道吗?
言真步履匆匆走进来的时候,整个宴会厅都好像静了一霎。倒不算因为她这个人有多么令人屏息,只是去年她凭着一条录音掀翻整个柏氏,又帶出一串官员受贿事件的壮举太过惊天动地,以至于人人自危。
听闻她最近报道了一起商业受贿案件,牵出整整十三人锒铛入狱。如今穿着黑风衣出现,不苟言笑,犹如一尊煞神。
在她出现的一瞬,柏溪雪明显感觉身边的人不自在地整了整领帶。
但她脱下风衣,露出珍珠白的丝质套裙,气质却又随之一变。
温秀明洁,还是柏溪雪熟悉的那种感觉。
教人恨得牙痒痒。
柏溪雪脸上挂着笑,任凭应流苏甜甜蜜蜜地挽着她臂膀,从牙齿里挤出声音道:“那又如何?”
应流苏却又不说话了,她眼波潋滟地飞了柏溪雪一眼,才答:“不如何。”
“你会感谢我的,”应流苏替柏溪雪理了一下发丝,动作亲昵,似一对璧人,“拜拜啦。”
她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只剩柏溪雪安静地回到自己的位置,言真坐得离她们很远,柏溪雪抬头看去,只见她带着笑,正同身边的人交谈,仿佛根本没发现她这边的异样。
柏溪雪便也慢慢地转回身去。
后来她们也没说上话。宴会散场时应流苏已经喝大了,挂在柏溪雪嘀嘀咕咕背台词,直到她经纪人扑过来扯走她,柏溪雪才终于得到解救。
酒过三巡,她也喝得脸上泛起了薄红。走到门口时卢镝菲托了她一把,问要不要送她走,柏溪雪笑嘻嘻的,还没说话——
面前却已经停了一辆车。
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开到了她们身边,摇下车窗,脸上没有什么笑意:“上车。”
卢镝菲剛要说话,她已飞快瞥了她一眼:“不是你。”
“柏溪雪,”她又转过去看她,目光幽深地重复,“上车。”
柏溪雪注视她三秒,忽然笑了一声,拉开车门。
车门啪地关上,车内极静,言真不看她,只专心致志地开车:“怎么喝这么多?”
柏溪雪轻轻地窝在副驾驶座上:“我想喝就喝。”
“你倒是和卢镝菲还有应流苏熟悉了起来,”她平静地说,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和,眼睛深处却隐隐有火苗跳动,“你们打算上哪去?”
“我送你。”
如果是以前的柏溪雪,她一定会反唇相讥说少管我,但这一刻,她也静了下来,或许是喝醉了,目光落到遥远的地方,慢条斯理说:“你猜?”
回答她的是一声刹车。
言真一把揪住她的衣领,将她扯过来,狠狠地咬住了她的唇。
安全带发出声响,柏溪雪下意识挣扎了一下,旋即便被对方用力地捏住了手腕。
啪嗒。安全带被言真用手松开,柏溪雪睁大双眼,一瞬间失去了重心——言真竟直接将她的座位放倒了。
她跨过来,居高临下骑在柏溪雪腰上。柏溪雪仰起头,看见对方眼中灼灼的焰,想要说些什么,下一秒,言真已再一次俯下身,以吻封缄。
黑风衣覆盖下来,成为一整片黑夜。带起衣物摩擦的窸窣声。柏溪雪茫然地抬起头,看见对方幽深的眼,凝视她如凝视一只陷入深渊的猎物。
脖颈被扼住了,唇舌将话语搅得支离破碎,只剩下喘息。那双洁白修长的手拢住咽喉处,慢慢收紧、收紧,让柏溪雪从此再难逃脱。
像决意钉死一只蝴蝶。
柏溪雪无法呼吸了,只能仰仗言真每一次唇齿交缠间渡过来的氧气。她试图夺回主导权,手腕却再一次被对方禁锢住,言真的牙齿报复性咬过她的唇,带着恨意,强硬不容拒绝地厮磨,直到唇瓣红肿。又被湿润的舌舔舐安抚,耳边响起小小水声。
两人的气息都交缠在一起,一时吻得难舍难分,心跳却比这更强烈。柏溪雪目光迷离,心神都被这一个激烈而凶狠的吻所摄,也不知道被吻了多久。
直到所有氧气都消耗殆尽,她终于蒙受怜惜,言真松开禁锢,喘着气,同她微微拉开了距离。
借着夜色微弱的光线,柏溪雪看见她胸膛剧烈起伏。
明明眉梢眼角都已经透着晕红,仍要冷冷地看柏溪雪:“不准去。”
“不准和卢镝菲去。也不准和应流苏去。”
她依旧撑在柏溪雪身上,咬牙切齿地说。
居然还在记着剛才的事儿。她语气凶狠,柏溪雪却心里轻轻笑了,感受到身上力道渐松,她故意装傻,只仰起头问:“凭什么?”
对方仍在思索,她抓住着迟疑的一瞬,一个翻身,瞬间将对方压在了身下,同样紧紧扼住了言真的手腕。
言真动弹不得,气得咬她:“柏溪雪!你不要脸!耍赖!”
“你才是耍赖!”柏溪雪被她咬得倒吸一口凉气,用腿狠狠钳制她挣扎乱扭的腰,想起这么多个没见面的日子,恨不得从她身上咬一口肉下来,却又舍不得,只好小学生一样地同言真吵嘴:“你凭什么管我?我没名没分的,难道你是我金主?”
“是又怎么样!”
言真尖叫,话音剛落便意识到自己说漏嘴——真是气昏头了!她懊悔咬住嘴唇,心里警铃大作。三十的人了,怎么还能在这里菜鸡互啄?
她瞥柏溪雪一眼,心里祈祷对面最好是真正的小学生,喝醉了脑子不好使,听不懂她说什么。
言真抿了抿唇,试图转移话题,柏溪雪却没有放过她这一点迟疑。
——不如说,她上一句话就是为了诈她。
柏溪雪猫一般危险地眯起眼睛:“所以,那部话剧是你投的喽?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