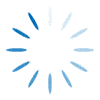“但这些都只能提供一个方向参考,”她无奈地笑了笑,“强行煽情,很容易惹人厌烦。”
柏溪雪点点头,她听进去了,但还是忍不住又一次試圖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:“就像以前拍戏,明知这段是伤心,但最强烈的情绪反而需要最克制,否则就变滥情。”
她孔雀开屏般分享自己的片场心得:“我们要让眼睛的情绪自己开口说话。”
“对,作为记者,就是力求让事实自己开口说话,”言真点头,思忖,“我要把这句放进这小孩的批注里去。”
“……”
言真又开始敲键盘,全没有注意到背后柏溪雪幽怨的目光——算了!
跟一个生日愿望都要许“今年的稿子全不被ban”的工作狂没什么好说的!柏溪雪在心里安慰自己,气鼓鼓地洗澡去了。
等到言真终于摘下眼镜,从书房出来时,便看见柏溪雪窝在沙发上,漂亮的臉蛋面无表情,一副“我要气壞自己心疼死你们”的模样。
大小姐这又是怎么了?言真失笑,走过去坐下,试图摸摸她顺毛。
柏溪雪瞥她一眼,随即就往旁边一闪,让言真的手扑了个空。言真又挪过去一点,柏溪雪便又往旁边躲。
言真再挪,柏溪雪再躲。像那种摸哪里,哪里就会凹下去的猫。
言真受不了了,眼疾手快,一把抓住了柏溪雪的睡袍。
柏溪雪嗷地叫了一声:“耍流氓!”
言真大吃一惊:“我怎么你了?”
“你扯我腰带,”柏溪雪振振有词,一下子来劲了,“你耍流氓!”
哪门子的歪理邪说啊!言真被气笑了。
然而,眼睛扫过去,却又觉得柏溪雪说得不无道理——她刚刚洗了澡出来,尚带水汽温热,身上只着一件絲质睡袍,隐隐勾勒出身形细腻的起伏。
而腰间衣带,正被她抓在手上。真丝柔滑,那个结柏溪雪打得也松,刚刚被她一扯,已经在松开滑落的边缘,衣领荡开,露出大片肌肤。
雪白细腻,仿佛有热气扑到言真臉上。而柏溪雪就这样窝在沙发衣角,委屈又柔弱地看她:“你还说你不流氓。”
柏溪雪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了,苦苦盼望她复出的铁杆影迷们,大概做梦都猜不到,大小姐白天在谈判桌上尔虞我诈,晚上就全把演技挥洒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。
但言真还是臉红了。她在心里咬牙切齿的唾弃自己,言真啊言真,再这么没出息下去,你就一辈子被小女孩撒娇骗吧!
撒娇的漂亮小女孩正仰着脸看她,睫毛又翘又长,娇气得很。
她覺得自己在这一瞬间鬼迷心窍,情不自禁俯身过去吻她。
这个吻一倾身便被捕获,柏溪雪勾着她脖颈,下压,将吻深入,柔滑的舌尖轻轻扫过她的上颚。
她果然开始轻轻喘起来,表情却有些出神。
——其实哄柏溪雪是她最擅长的事,毕竟这么多年,她一直都在做,只是过往总封闭着感情,全心全意做柔顺金丝雀,予取予求,反倒熟稔简单。
但现在,一切都不同了。她反而笨拙起来,青涩又迟疑地思索着自己身体的反应——这样做是合适的吗?会不会又陷进过去那种情绪里?
其实言真很怕自己的身体本能已经习惯按部就班,总覺得这样对柏溪雪不公平。
言真胡思乱想,柏溪雪留心到她忽然紧绷的动作,指腹安抚性地揉了揉她的腰,低声问:“怎么了。”
言真有些支吾:“我只是……”
她垂下眼睛:“有时候,我会有点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好。”
柏溪雪惊异地睁大了眼睛,随后,心脏便刺痛一下。
她当然知道言真在说什么,是她从前太坏,总是欺负她那样狠,以至于如今每次接吻到情动的时候,言真总会抓着她的衣领,显得有些怯怯的怕。
柏溪雪放柔了动作,手掌又轻又缓地在她肩膀处打转,摩挲圆润的肩头,声音也放得很轻。
“没关系的,你不要用‘表现’这样的词。”
“我只是想看见你开心而已,”她柔声道,缓慢地吻啄言真的脸,不动声色地调转了姿势,将对方放在身下,又小心翼翼地撑起身子,怕压到她,“我喜欢看见你舒服的样子。”
柏溪雪用呢喃的声音说。
言真点了点头:“嗯……”
表情却分明是还有点迟疑。柏溪雪不再说话,只是俯下身去,吻吻她的唇:“现在是什么感覺。”
“嗯,”她思索了一下,“软软的。”
柏溪雪又啄了一下她泛着粉意的脸颊:“这样呢?”
“有一点痒……呜!”
这是耳朵被柏溪雪吹了口气,她鸦羽般的睫毛垂了下来,专心致志地看言真,让气流又软又轻地打着旋儿,拨动发丝,一直吹到言真粉透的耳朵里:“这样?”
身下的人身体已经打顫了:“好、好痒,别、这样……柏溪雪……呜……”
耳垂被含住了,柏溪雪埋头在她发间,一心一意拨弄、吮吸柔软的耳垂,手掌摸到衣摆,很好的真丝料子,却远不如言真的肌肤软腻柔滑。
即便如此柏溪雪还不放过她:“这样呢?”
言真说不出话了,她断断续续呜咽,支支吾吾求饶,在被吻的间隙发出一些可怜又糟糕的声响。柏溪雪被她抓住肩膀,知道她已经被亲懵了,俯身在她耳边,哄诱般低声说:“言真,你这样就很好。”
不是假话,她低头吻言真鼻梁上那点小痣。言记者有挺秀的鼻梁,明亮坚定的眼睛,工作时总会微微蹙眉,神色又清又冷又锐利。
但现在冰霜都化了,她依旧蹙眉,眼角却泛红,生理性泪水叫人眼眸湿润,难耐又纵容地看着柏溪雪,已被吻至失神。
也只有柏溪雪能看到这样的她。
“言真,”而柏溪雪的声音中仿佛有某种魔力,明明是小声的呢喃,却让言真耳朵发痒,“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可爱。”
可爱?她茫然地看着柏溪雪,又被揉了揉不该揉的地方,显然是不知道。
柏溪雪已经有些受不了,她的手指轻轻绕着言真的发尾打转,最后一次凭着理性问:“你的稿子改完了吗?”
问还是要问的。她心里幽怨地想,要是耽误了工作,言真肯定跟她拼命。
工作狂现在正无辜地看她,明明还是情迷意乱的神色,但负责上班的那部分脑子显然已经本能地动了起来,想也不想地点头,声音很有把握:“改完了。”
……受不了了。柏溪雪哼一声,将她打横抱起,往房间走去。
言真吓得一下子勾住她的脖颈,又变成小小声:“去哪里……”
“去浴室,”柏溪雪的手托住她臀部,另一手护住她的背,亲亲昵昵的,还是用那种小女孩撒娇的音调,“那里有镜子。”
柏溪雪低头亲她,用商量的语气哄骗:“我想让你也看看自己有多可爱,好不好?”
于是言真又鬼迷心窍。
直到被放到盥洗台上,她才知道错了。
做金丝雀的时候,言真就很少来B市,因此也不知道如今这套房子是柏溪雪曾经的置业,还是一切洗牌后新购入的房产。
大概是新的,因为浴室内并没有太多生活过的痕迹,宽大的盥洗台上物品极少,干净得甚至有一丝冰冷,显露出主人已经改变的生活气质。
也很方便将人放到上面品尝。
整套房子都是中控的,浴室的温度已预先上调,言真的手摸到温热的大理石板,心里咬牙切齿,心道谁家正经人会给盥洗台装温控系统。
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
但她无从辩驳柏溪雪明晃晃的坏心眼,毕竟,今晚的一切都是她默许纵容,心知自己有一万次机会抽身而退,但却偏偏选择了共沉沦,一次次仰着头,任柏溪雪落下一个又一个的吻。
如今,她也咬着嘴唇纵容柏溪雪握住她腿弯,指腹摩挲,打转。
在这点上柏溪雪也像小女孩,总喜欢轻轻摸摸这里,亲亲那里,接吻时手指要绕着她发稍打转,很是黏糊。
言真总是被她缠磨得没有办法,便只好任她挑动敏感的神经末梢。
……台面铺了柔软的毛巾,因此跪上去也不会觉得难受。
镜子忠实地映照眼前的一切,绯红的雪白的,分开的闭拢的都展示得一览无余。
丰盈的生理感受化作烟花在大脑爆炸,她顫抖,却又听见身后的人慢条斯理地说:“言老師。”
“猜我在用哪只手?”
其实不需要猜,因为一抬头就能清清楚楚、分分明明地看到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