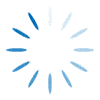叶凌波闻言一怔,眉峰微蹙,将其中利弊从头到尾忖度了一番。再抬眼时,见苏锦绣神色笃定,眼底毫无半分怨怼与疑惧,悬着的心才缓缓落地。
她轻轻拍了拍苏锦绣的手背,又气又无奈地叹道:“你们啊……罢了罢了,虽惊世骇俗,倒也是眼下最管用的法子。”
苏锦绣先前在逢府曾习得几分点茶绝技,此刻便引着叶凌波往茶厅漫步。
炉上清泉沸鸣,她取了龙团胜雪,碾末、过罗、注汤,茶匙轻搅间,乳白浮沫渐起。
她一边专注打茶,她一边续道:“母亲有所不知,二郎纳的十房美妾,原是醉春坊一众想脱贱籍的名伶头牌。前番接入府中不过是掩人耳目,转瞬间便已放她们归去。不仅让她们弃了艺名,重拾本名,还遣人送离汴京,另寻安身之所,外人自然无从知晓。再者,每位都给了数倍于寻常人家的资财,足够她们安稳过几辈子了。”
叶凌波望着盏中细腻的沫饽,听着这番周密安排,不由得轻叹:“你们这般同心一体,遇事又能这般周全考量,想来再大的难事也能从容渡过。倒是我瞎操心,平白添了许多忧虑。”
“哪能是瞎操心呢?”苏锦绣捧着茶盏,仰头冲叶凌波笑眼弯弯,眼底满是孺慕,“有母亲这般疼惜关怀,便是日后真遇着什么不妥,想来也有母亲为我撑腰照料,我心里欢喜得紧呢。如今只想着多在母亲跟前撒撒娇,让母亲多疼我、多惯着我才好。”
叶凌波被她这番软语说得心头熨帖,抬手轻轻点了点她的鼻尖。
茶厅内茶香氤氲,伴着二人的笑语盈盈,暖意融融,满室舒心惬意。
与叶凌波叙罢家常,苏锦绣便动身返回镇远侯府。依着莫辞的指引,知晓闻时钦在书房理事,她遂径直往书房而去。
未及门前,便听得屋内传来一阵男子的哭嚎声,嘶哑凄厉,不似闻时钦的声息。苏锦绣心下生疑,抬指便轻叩门扉。
门应声而开,闻时钦立在门内,一身玄色窄袖蟒袍,金纹暗绣,勾勒出挺拔身姿,面容却凝着几分冷冽。
苏锦绣目光越过他往屋内探去,却见地上匍匐着一人,正撒泼打滚、涕泗横流。
她当即拨开闻时钦的臂弯,莲步轻移入内,便见地上那人哭得力竭,侧身躺卧,双手死死掩面,不肯展露半分容颜。
苏锦绣蹲下身,越瞧越觉身形熟稔,索性伸出纤纤玉指,轻轻掀开他的手。
竟然是谢鸿影。
谢鸿影一见是她,像是溺水之人得遇浮木,猛地攥住她的手腕,哭喊不已:“巧娘!巧娘救我!”
苏锦绣被他这狼狈模样惊得一愣,转头望向立在门旁、神色冷冽的闻时钦,复又回眸看向泪眼婆娑的谢鸿影,不禁蹙眉问道:“这是怎的了?怎会弄成这般模样?”
她直起身正要追问缘由,谢鸿影却猛地扑过来,死死抱住她的小腿,哭哭啼啼不肯松手。
闻时钦见状,一股无名火直冲斗牛,随即眉峰倒竖,冷喝一声:“放开她!”
“我不放!死也不放!”谢鸿影哭得涕泪横流,死死箍着她的腿,“我不要参军!闻时钦,我招你惹你了?你凭什么把我这兄弟往军营里送?我好不容易自青州脱身,只想过几天好日子,我不要去当兵!巧娘,你快救我!我真的不想去!闻时钦,我恨你!”
苏锦绣一时茫然无措,然她深知此事绝非无的放矢,于是她欲拉谢鸿影起身,奈何他抱得紧实,她弯不得膝,只能碰到了他的脸颊。
这一幕落在闻时钦眼里,却宛若她在温柔抚摸安慰谢鸿影,他攥紧拳头,破天荒地直呼了其名。
“苏锦绣!”
苏锦绣心头一跳,连忙收回手,直起身干笑两声,又转向地上的人:“鸿影,你先起身,有话不妨从长计议,我替你周旋便是。”
谢鸿影这才单手死死拽着苏锦绣的裙裾,抽抽噎噎起身,躲在她身后,避闻时钦如蛇蝎。
闻时钦叉着腰别过脸缓了一会,随后压下心头翻涌的火气,缓声道:“谢鸿影,此番遣你去历练,前路我已探明。这队兵士不过是应对一场小股寇匪的侵扰,绝非九死一生的恶战,你且放心,我已妥为部署,绝无性命之忧。”
“纵是无虞,我也不欲去!”谢鸿影梗着脖子,语气仍带着执拗。
闻时钦眉峰一挑:“此事由不得你。我已为你递了军籍文书,如今旨意只差临门一脚,你若执意推脱,便是抗旨不遵,届时可不是不去便能了结的。”
谢鸿影闻言,长叹一声,方才压下的哭腔再度爆发,对着苏锦绣哭诉:“巧娘,你瞧瞧他!如今他越发无法无天,竟连我的去路都要摆布!巧娘,我真的不想去,那军营之地,岂是我这等闲散人能待的?”说着,便要扑上前去抱苏锦绣的胳膊。
闻时钦忍无可忍,跨步上前,一把揪住他的衣领,将人拽得离苏锦绣足有丈许远,力道虽重,恳切道:“你且信兄弟这一回!此番绝非害你,实是为你长远计!”
苏锦绣无奈,只得耐着性子温言劝抚谢鸿影,许了他三日之内必有交代,才总算将这缠人的主儿送走。
折返书房时,却见闻时钦指尖捏着一只白瓷茶盏,盏身已裂出数道细纹,他静坐案前,面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,目光沉沉锁着她。
苏锦绣刚迈步上前,便被他猛地揽住腰肢拉近,旋即被稳稳置于膝上从后方围抱住。未等她反应,他俯身便往她纤细的脖颈处咬了一口,带着泄愤的力道。
苏锦绣吃痛,抬手拍了他一下,蹙眉嗔道:“你这是怎的了,平白发疯?谢鸿影本就不是吃军营苦的料子,你何苦这般逼他?”
闻时钦伏在她颈间,呼吸粗重灼热,带着难言的委屈,闷闷问道:“阿姐,你也觉得我不讲事理,是无缘无故把他往火坑里推,是不是?”
苏锦绣心底暗忖,可不就是如此?
但见他这副沉郁又带些执拗的模样,知晓他此刻心头正憋着气,若是直说,指不定还要再咬自己几口,遂语气放柔:“自然不是。你向来行事有分寸,这般安排,定是有你的缘由,不妨与我说说?”
闻时钦伏在她颈间,呼吸粗重得烫人,被满心翻涌的醋意与委屈裹挟,不知如何措辞——总不能道破前世谢家满门抄斩的惨状。
他分明查清了底细,谢家靠漕运积财,却无官身庇护,早被漕运总督一系视作肥羊,暗中伪造账目,诬陷谢家私吞朝廷漕银。那笔被觊觎的银子本是谢家周转之资,如今成了抄家灭族的祸根,唯有让谢家以资助军需名义捐作军饷,再让谢鸿影主动投军,这样既能给银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去向,堵住构陷者的嘴,更能借军籍护住谢家满门。
闻时钦低头,又在她颈间狠狠咬了一口。
“阿姐,”他声音沙哑,满是不甘的怨怼,“你是不是心疼他?是不是觉得我无理取闹,逼着他做不愿做的事?”
闻时钦抬手,指尖用力捏住苏锦绣的下巴,迫使她抬头看着自己,语气又酸又涩:“我方才算是看清了。你能这般温言软语抚慰我,也能这般耐心哄着旁人,倒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个好弟弟要护着?先前我还傻傻以为,你待我是不同的,原来都是一样的周全体贴。我真是被你骗得好苦!”
“你胡说什么!”苏锦绣又气又笑,抬手戳了戳他的额头,“我哪有那么多好弟弟?自始至终,不就你一个吗?”
闻时钦眼眶都红了,只差没气哭,偏头躲开她的手,语气带着浓浓的委屈与执拗:“我看得清清楚楚!你摸他的脸,还耐着性子哄他,他抱着你腿哭,你也不推开!原来这阿弟的位置,从来不是我一人的,全是我一厢情愿罢了!”
闻时钦说罢,竟抬手捂住脸,肩膀微微发颤,倒像是在暗自垂泪。
苏锦绣坐在他腿上,只觉哭笑不得。两人早已情根深种,肌肤之亲、山盟海誓皆已过,只差临门一脚的婚嫁,他竟还揪着这点小事钻牛角尖。她一时竟不知如何辩解,只能软着语气唤他:“阿钦……”
话音刚落,闻时钦猛地放下手,眼底还带着水光,却骤然翻起了旧账,语气又酸又硬:“哦,我倒想起来了!先前我们还没走到一处时,你不就想嫁谢鸿影吗?差一点就真嫁了!你还当着谢夫人的面夸他,说他是世间最好的儿郎!”
他发颤控诉:“那日在谢府的假山底下,你说的每一个字,我都听得明明白白!”
苏锦绣张了张嘴,万万没想到他竟翻出这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,结结巴巴道:“你、你当时在?……那都是多少年前的糊涂话了!”
“糊涂话?”闻时钦抬眼,眼底水光未散,语气却带着尖刻的酸意,“当日若不是我豁出去对你发脾气、掏心窝子,凭你这温软性子,怕是早抵不住谢夫人三番五次的撮合攻势了!是不是我今日,还得恭恭敬敬叫你一声谢夫人?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